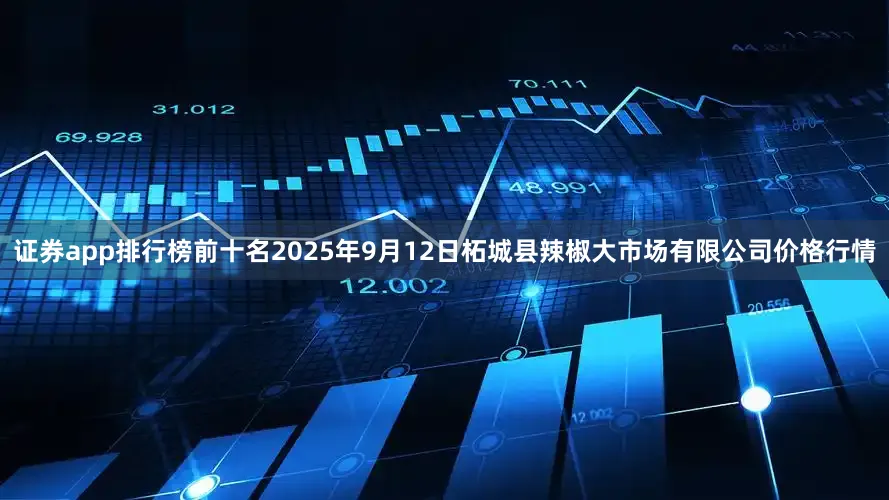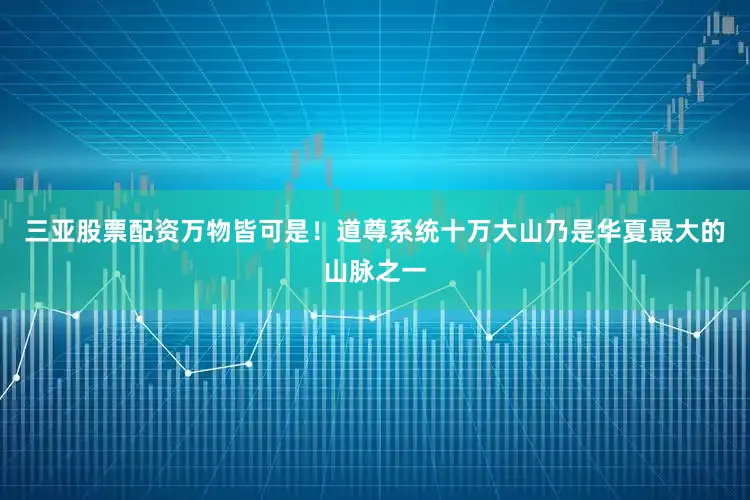1968 年的春天,陕西汉中留坝县的山花开得正艳。我出生在马道镇一个叫 “徐家沟” 的山村,地无三尺平,出门就是爬坡。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一辈子没走出过县城,却总在我耳边念叨:“超娃,咱这山沟养不住人,你将来一定要出去。”
家里四个孩子,我是老大。7 岁那年,我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,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去公社上小学。教室是土坯房,课桌是裂开的木板,老师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。但我学得格外卖力,父亲说:“读书是咱穷人唯一的出路。”
1984 年初中毕业,我考上了隔壁镇的高中,却在报到前一夜撕了录取通知书。母亲在油灯下哭:“超娃,你咋这么傻?” 我望着炕桌上弟弟妹妹的课本,咬着牙说:“娘,家里供不起,我去挣钱供他们。”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只能在山里刨食了。
1986 年冬天,征兵的消息传到村里。我揣着两个窝窝头,走了四十里山路去公社报名,却因为体重不够被刷了下来。
回家的路上,我坐在汉江边上哭了一下午,江水冻得结了薄冰,像我冰凉的心。1987 年冬天,我又去了这次我揣着母亲煮的鸡蛋,硬是在报名前多吃了三个,又猛灌了一肚子水,就这样憋着尿体检,不过幸运的是总算过了体检这一关,随后的政审,家访等环节也顺利通过。
展开剩余88%拿到《入伍通知书》那天,父亲把他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塞给我:“在部队好好干,别惦记家。” 我抱着收音机,在院子里给父母磕了三个头,背上背包走出了徐家沟。那时我还不知道,这一走,不仅走出了山沟,更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。
内蒙古的边防比想象中苦。我们驻守在中蒙边境,冬天零下三四十度,巡逻时睫毛都能冻成冰碴。我的任务是防范走私和非法越境,每天要在雪地里走几十里,枪膛冻得拉不开栓,就用体温焐热。
当新兵的第一个冬天,我因为冻伤住进了卫生队。班长来看我,从兜里掏出个苹果:“建超,咱当兵的,这点苦算啥?” 那个苹果冻得硬邦邦,我啃得眼泪直流,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苹果。
1988 年夏天,我们配合地方搜捕一伙走私犯。在草原上追了三天三夜,水喝完了就喝露水,干粮吃完了就啃草根。最后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堵住了他们,我凭着在山里练出的灵活身手,第一个冲进去按住了头目。那年年底,我入了党,还升了副班长。
1989 年冬天,我成了班长。手下有六个新兵,最小的才 17 岁,想家想得直哭。我把母亲寄来的腊肉分给他们,给他们讲徐家沟的故事,告诉他们:“咱当兵的,要把想家的力气用在训练上。” 那两年我们班拿了三次 “先进班集体”,墙上的奖状贴满了一面墙。
1991 年 12 月,我退伍了。五年军旅生涯,我没立过大功,没学过技术,只带回了 320 块退伍费、医疗补贴和攒的津贴。
离开营区那天,战友们送我到车站,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建超,到了地方好好干,别给咱边防兵丢人。” 火车开动时,我望着窗外的草原,眼泪止不住地流,那里有我最热血的青春。
1991 年 12 月的汉中,飘着细碎的雪花。我从火车站出来,步行去汉运司买回家的车票。候车室里挤满了人,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和汗味。我攥着兜里的 320 块钱,心里盘算着:给父母买两斤红糖,给弟弟妹妹买几本作业本。
就在我排队买票时,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哭喊:“我的钱!我的钱被偷了!” 我回头一看,一个穿着蓝色棉袄的大爷蹲在地上,双手抓着头发,肩膀抖得厉害。他的棉袄袖口磨破了,毛衣领子上有个洞,一看就是苦日子过来的人。
保卫人员过来登记,大爷哽咽着说:“我要去西乡投亲,钱装在手帕里,藏在棉袄内袋,咋就没了呢?”
周围的人议论纷纷,有人说 “车站小偷多”,有人说 “这人看着就老实,咋这么倒霉”,却没人上前帮忙。
我看着大爷,突然想起了父亲。父亲也是这个年纪,也是这么老实巴交,要是他出门遇到这事,该多着急?我摸了摸兜里的钱,咬了咬牙走过去:“大爷,您去西乡?” 他抬起头,眼睛红得像兔子:“是啊,闺女让我去过年。”
“我帮您买票。” 我没多想,拉着他去售票窗口,买了一张汉中到西乡的车票,又从兜里掏出 15 块钱:“大爷,这钱您拿着路上买吃的。” 他愣了半天,突然抓住我的手:“娃啊,你叫啥?家住哪?我一定要还你!”
我被他攥得生疼,笑着说:“大爷,不用还,谁出门还没个难处?” 他却不依,非要我留下地址。我拗不过他,就在他的烟盒纸上写下:“留坝县马道镇徐家沟 徐建超”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烟盒纸折好,塞在内袋里,拍了又拍:“娃,你是好人,老天爷会保佑你的。”
车上的人有人说我傻,有些人还说这个老爷子是惯犯了,经常在这里行骗,我肯定是被他骗了,老人拿到车票后肯定会转手卖给其他人。
对此我不以为然,我始终不相信老爷爷是骗子。
那天我坐上车,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,心里暖暖的。在部队五年,我们帮驻地老乡挑水、种地、修房子,班长说:“当兵的,就是要帮老百姓。” 我觉得这点小事,不算啥。
回家过年后,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二弟在学木匠,三弟上初二,小妹上小学,家里的开销全靠我。母亲总在夜里叹气:“超娃,是家里拖累了你。” 我笑着说:“娘,我是老大,该我扛。”
1992 年春天,我去汉中城里找活干。在黄家塘的货运站找到了卸货的活,每天扛大包,累得倒头就睡,一天能挣 15 块。有次我扛着一百多斤的化肥,脚下一滑摔在地上,化肥撒了一身,老板还骂我笨。我躺在地上,望着灰蒙蒙的天,突然想起内蒙古的草原,那时虽然冷心里却亮堂。
干了一年,我跟着老乡去了广州。在制衣厂上班,每天干十二个小时,流水线转得像风火轮。我负责钉纽扣,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,下班时连筷子都握不住。半年后,我的腰出了问题,疼得直不起来,只好辞了职。
在出租屋里躺了半个月,我去找了份仓库保安的活。工资不高,但清闲,能趁机学点东西。仓库里有个叉车司机老常,也是退伍军人,我就缠着他教我开叉车。老常被我磨得没办法,趁没人时偷偷教我:“建超,咱当兵的,就得有股韧劲。”
1994 年夏天,我考到了叉车证,进了一家电子厂开叉车。工资涨到了每月 800 块,我终于能给家里寄更多钱了。三弟写信说:“哥,你放心,我一定考上大学。” 小妹也寄来她的奖状,说要向我学习。我把信揣在兜里,开叉车时都觉得浑身是劲。
可日子刚有起色,麻烦就来了。1996 年春节回家,二弟带着怀孕的对象上门,女方家要 5000 块彩礼,不然就去告他。
母亲急得直哭,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,一句话不说。我把攒的 3000 块全拿出来,又找战友借了 2000,总算把这事了了。
送二弟去女方家那天,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28 岁的我,没房没存款,还是个大龄青年,父母急得托人给我介绍对象,可人家一听我要供两个学生,都摇头。我望着徐家沟的方向,第一次觉得人生这么难。
离开家的前一天,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信。信封上的地址是 “留坝县马道镇徐家沟 徐建超收”,寄信人是 “汉中汉台 胡勇”。我愣了半天,想不起这是谁。
拆开信,里面掉出一张 50 块钱和一张纸条。字迹歪歪扭扭,却写得很认真:“建超娃,五年前在汽车站多亏你帮忙,我找了你五年才找到地址。
这点钱你一定要收下,不然我心里不安。如果你方便,正月十六来汉中汉白路‘胡记面皮店’,咱爷俩见一面。”
我突然想起那个穿蓝色棉袄的大爷!原来他叫胡勇。拿着信我心里又暖又酸,其实我早把这事忘了,他却记了五年,还费这么大劲找我。
正月十六那天,我坐最早的班车去了汉中。汉白路上的 “胡记面皮店” 不大,门口支着两口锅,一个穿着围裙的姑娘正在烙面皮,香气飘出老远。看到我进来,姑娘笑着问:“您是徐建超大哥吧?我爹等您半天了。”
里屋走出个大爷,头发白了不少,却精神矍铄。一见到我,他就拉着我的手:“建超娃,可算把你盼来了!” 他就是胡勇这五年,他一直在找我。
原来那天我帮他买票后,他去西乡过了年,却把写着我地址的烟盒纸弄丢了。他只记得我叫徐建超,是留坝马道的,就每年春节给马道的两个村子寄信,直到今年年初,才有个老乡告诉他:“徐家沟是有个徐建超,在广州打工。”
“建超娃,你是好人啊。” 胡大爷给我端来一碗热面皮,“我小女儿胡丹,前两年离婚了,现在跟我开这个店。她人勤快,心眼好,就是命苦……”
正说着,刚才烙面皮的姑娘进来了,脸颊红扑扑的,手里端着一盘炒花生。“这是我闺女胡丹。” 胡大爷介绍道。胡丹冲我笑了笑,眼睛弯得像月牙:“徐大哥,常听我爹提起你。”
那天我们聊了很久,我讲了这五年的打工路,他讲了胡丹的遭遇。胡丹初中毕业后去西乡帮厨,嫁给了一个供销社职工,没想到对方好赌还家暴,她硬气地离了婚,带着积蓄回汉中开了这家店。
临走时,胡大爷突然说:“建超娃,你觉得小丹咋样?我看你俩挺合适的,如果你不嫌弃她二婚,我赞成你们处对象。” 我愣在原地,胡丹红着脸跑了出去,店里的炉火 “噼啪” 响,我的心跳得像打鼓。
回广州的火车上,我满脑子都是胡丹的笑脸。她烙面皮时专注的样子,给我端花生时羞涩的样子,都刻在了我心里。半个月后,我鼓足勇气给她写了封信,把从小到大的经历、打工的苦乐、家里的负担,一股脑全说了。
没想到,胡丹很快就回信了。她说:“建超哥,我不嫌你家负担重,也不怕吃苦,只要两个人心齐,日子总会好的。” 信里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,穿着的确良衬衫,笑得阳光灿烂。
我们开始通信,一封又一封。她跟我说店里的生意,说汉中的变化;我跟她说厂里的趣事,说广州的繁华。信纸成了我们之间的桥,跨越千里,把两颗心连在了一起。
1997 年春节,我提前回了家。在面皮店里,我和胡丹说了很多心里话。她说:“建超哥,我跟你走,去广州也行,留汉中也行。” 我说:“小丹,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”
正月初八,我们领证结婚了。没有大操大办,只请了几个亲戚,胡大爷给我们做了一桌子菜,喝到兴头上,他抹着眼泪说:“小丹,你总算找对人了。” 我给父母说胡丹是初婚,怕他们老思想想不开,胡丹笑着说:“没事,以后他们会知道的。”
婚后,胡丹继续在汉中开店,我回广州打工。我们商量好,等她房租到期就去广州,开家陕西面皮店。1997 年 8 月,三弟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,胡丹特意回徐家沟给他办了升学酒,在酒席上,她给弟媳塞了个红包:“好好养身子,孩子出生我来帮忙。”
10 月份,胡丹来了广州。我们在制衣厂附近租了个小门面,“胡记面皮店” 开张那天,老乡们都来捧场。胡丹的面皮筋道,调料正宗,很快就火了起来。每天我下班就去店里帮忙,揉面、洗碗、收账,虽然累,心里却甜滋滋的。
1998 年 9 月,儿子出生了,我们给他取名 “徐缘”,意思是缘分的缘。胡大爷也来广州帮我们看孩子,一家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,却其乐融融。1999 年夏天,小妹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,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她给胡丹打电话:“嫂子,谢谢你和我哥供我。”
2000 年,我们把面皮店搬到了深圳,生意越做越好。2010 年,我们在深圳买了房,把父母也接了过来。父亲看着阳台上的花,笑着说:“超娃,你真走出山沟了。”
2020 年,因为疫情,我们关了深圳的店,回了汉中。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,胡大爷 85 岁了,每天还去店里帮着择菜,耳朵有点背,却总爱跟客人说:“我这女婿,是当年一张车票换来的好人!”
去年冬天,我和胡丹回了趟徐家沟。山还是那座山,水还是那条水,只是土路修成了水泥路。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胡丹笑着说:“当年你帮我爹买票时,想过会有今天吗?” 我握着她的手,看着远处的雪山:“没想过,但我知道,好人总有好报。”
书桌里的车票存根已经泛黄,信纸上的字迹也淡了,但那份善意带来的缘分,却在岁月里生了根,发了芽。人生就是这样,一个不经意的善举,往往会开出最甜的花,结出最暖的果。
发布于:广东省美林配资-软件炒股杠杆-网络配资平台-安全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